放大资金,增加盈利可能
配资是一种为投资者提供杠杆资金的金融服务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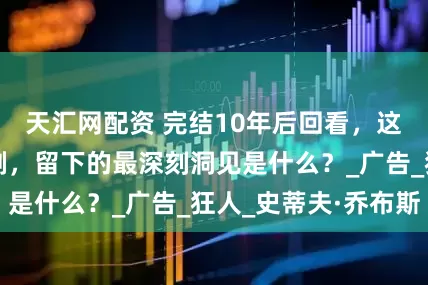
《广告狂人》这部兼具视觉魅力与深刻反思的经典有线剧集,最近终于悄然登陆Netflix,重新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。剧情尚且不提,仅仅是开场的第一幕便足以让人迷醉:一位西装革履的黑发男子独自倚坐在酒吧里,酒杯碰撞声清脆响起,服务生擦燃火柴点燃香烟——这一瞬间的画面,恍若一剂视觉迷药,将人瞬间带入一种无可抗拒的恍惚与愉悦之中。这场景仿佛投射出1960年代纽约的浓烈色彩,一种带有强烈诱惑力的美学毒品。而剧集的创作者马修·韦纳,为我们呈现了一颗璀璨的瑰宝:明亮、炫目,布满了人人梦寐以求的中世纪风格家居,令人无法抗拒。
我记得当年我便完整地追完了这部剧——从2007年首播到2015年最终季播出。尽管它一直在我记忆的某个角落潜藏,但直到今天,我依然没有再度重温。那是一个电视剧正在逐步超越小说,成为文化高峰的时代,《广告狂人》作为那股“神剧潮”中的佼佼者,无疑闪耀其中。
剧集的七季剧情围绕唐·德雷柏展开——一个出身贫寒、风流成性,却在麦迪逊大道广告圈中举足轻重的创意天才。1960年代,正是从五十年代的压抑保守走向七十年代个体主义的关键十年。性解放、女性主义、民权运动……这些在今天被视作常识的道德观念,最初的雏形便诞生于那个时代。因此,《广告狂人》成了多个社会解读的样本,仿佛一面镜子,映照出当时社会的各种深层问题。
展开剩余76%如今,《广告狂人》完结已整整十年,我反而愈加对剧中“天才/操控者”的人设深感兴趣。在我看来,唐·德雷柏简直就是没有穿高领衫的史蒂夫·乔布斯。
故事开篇设定在1960年3月,那正是消费时代的起点。当时,公众被鼓励将购物视为自我表达的方式。在德雷柏担任创意总监的斯特林-库珀广告公司,广告人们并不单纯推销产品的功效,而是强调“品牌让你感觉良好”的心理暗示。如同德雷柏在第一集中对万宝路香烟的老板们所说:“广告的核心只有一个——幸福。你知道什么是幸福吗?是新车的气味,是摆脱恐惧的自由,是公路旁的广告牌大声告诉你:你现在的模样,已经足够好……”
如果你是首次观看此剧,或许可以跳过接下来的部分。到了第七季的尾声,德雷柏已经明显跟不上反主流文化的节奏。年轻一代不再满足于“你很好”的安慰,他们渴求的是叛逆、觉醒和灵魂的自由。然而,品牌又如何去卖这种东西呢?身处生存危机中的德雷柏,面对最大客户可口可乐的创意提案却遭遇瓶颈。他独自驾车横跨美国,最终来到加州的一个新时代精神疗养院,被迫直面内心深处的空洞。
最终一集以一种暧昧不明的方式结束:德雷柏似乎在那个公社中找到了某种灵感,随后画面一转,便出现了那支历史上经典的电视广告:“我想买瓶可乐给全世界”——即著名的“山丘顶”广告。问题随之而来:德雷柏是否找到了个人救赎?还是说,他只是意识到“和平、爱、共融”这些反叛理想,也能被包装和销售,就像卖新车的气味一样轻松?
事实上,这支广告在1971年首播后风靡全球,它的推出预示着现代品牌战略的重大转型。正如恩格斯堡思想网站的作者伊恩·莱斯利所指出:“到了70年代初,可口可乐品牌正面临着被新一代消费者视作五十年代遗物的风险……而麦肯广告公司推出的这支广告,毫不犹豫地将青年文化的叛逆能量进行了一次大胆的收割。结果大获成功。‘爱与和平’的理念被用来销售甜饮,瞬间让可口可乐显得充满青春活力。”
《广告狂人》的剧本创作始于2000年代初,恰逢史蒂夫·乔布斯正在重新塑造我们与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。“献给那些疯狂的人、不合群的人、叛逆者、麻烦制造者……”这句开场白由乔布斯亲自配音,出现在苹果的“非同凡想”广告中(1997至2002年播出)。若将这句话与《广告狂人》中某一集的对白放在一起,几乎可以互换。到了2007年,剧集首播的同一年,乔布斯发布了iPhone,并成功将“产品”包装成了文化身份的一部分,成为了自我表达的工具。而德雷柏最后出现在加州——距离苹果公司成立仅五年之遥——这一巧合,怎能不令人深思?这是否是一种对乔布斯以及后来一众“天才操控者”的致敬,还是对他们的某种讽刺呢?或许,两者兼而有之。
《广告狂人》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,便是它时不时戳破那些自命不凡的男人的虚妄。广告人们虽然居高临下,却常常身着过时的复古服饰,仿佛一群闯入错误片场的喜剧演员。至于那些所谓的“天才”,尤其是德雷柏,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,观众始终摸不清。他的一些广告创意的确能够打动人心(例如“它不叫‘轮子’,它叫‘旋转木马’”),然而也有不少被剧中人物奉为经典的点子,让观众一头雾水。难怪《纽约客》的前电视评论家艾米丽·努斯鲍姆曾戏谑道,德雷柏是“一个谜团,包裹着另一个谜团,外面再披上一张乔恩·哈姆的面孔”。
当然,这部剧也并非毫无槽点。2011年,《纽约书评》的丹尼尔·门德尔松曾对其进行过犀利批评,称《广告狂人》不过是“披上高级时装(和高级概念)的肥皂剧”。他认为剧作的文字较为单薄,那些看似深刻的“概念”其实充满了误导,哄骗观众误以为自己正在欣赏一部高文化含量的作品,实则不过是“像孩子翻玩具箱一样,玩完即丢”。
这番批评虽然尖锐,但也不无道理。剧中涉及种族歧视、性别不平等、同性恋权利等社会问题,但处理得时有波动,有时只是轻描淡写地掠过。《名利场》的记者乔伊·普雷斯曾在采访中称,这部剧呈现的是“六十年代底色之下的虚伪与腐化的时尚画像”,而韦纳本人也承认,“这部剧更关注的是‘无力感’,有时甚至为此牺牲了情节节奏。”
然而,《广告狂人》真正做得出色的地方,正是它揭示了消费主义文化内核的空洞,及那些自诩为“天才”的人物如何用一个个故事,将这些空壳包装并卖给我们——让我们相信,购买一瓶汽水、一部手机或一辆新车,便能获得幸福或觉醒。从60年代的麦迪逊大道,到2000年代的硅谷,甚至到今天科技与权力交织的社会,《广告狂人》早已悄然埋下了这条隐秘的线索。而剧中的家居布置,的确无可挑剔,值得一赞。
发布于:山东省联丰优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